内容详情
王充-生平介绍
作者:王充
王充是东汉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和教育家,他的哲学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: 1.天自然无为 王充认为天和地都是无意志的自然的物质实体,宇宙万物的运动变化和事物的生成是自然无为的结果。
他认为万物是由于物质性的气,自然运动而生成的,天地合气,万物自生,生物间的相胜是因为各种生物筋力的强弱、气势的优劣和动作的巧便不同,并非天的有意安排,天不是什么有意志能祸福的人格神。
2.天不能故生人 王充认为天是自然,而人也是自然的产物,人,物也;物,亦物也,这样就割断了天人之间的联系。
他发扬了荀子明于天人之分的唯物主义思想。
他说:人不能以行感天,天亦不能随行而应人。
他认为社会的政治、道德与自然界的灾异无关,所谓天人感应的说法只是人们以自己的想法去比拟天的结果。
3.神灭无鬼 王充认为人有生即有死。
人所以能生,由于他有精气血脉,而人死血脉竭,竭而精气灭,灭而形体朽,朽而成灰土,何用为鬼?他认为人死犹如火灭,火灭为何还能有光?他对于人的精神现象给予了唯物的解释,从而否定鬼的存在,破除了善恶报应的迷信。
4.今胜于古 王充反对奉天法古的思想,认为今人和古人相齐,今人与古人气禀相同,古今不异,没有根据说古人总是胜于今人,没有理由颂古非今。
他认为汉比过去进步,汉在百代之上,因为汉在百代之后。
这种见解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是完全对立的。
王充喜欢博览群书,但是不死记章句。
小时候家里穷没有书,经常去逛洛阳集市上的书店,阅读那里所卖的书,看一遍就能够背诵,于是精通了百家之言。
后来回到乡里,住在家里教书。
会稽郡征聘他为功曹。
”可见双亲俱在,且很慈爱,未尝见背。
王充少时,不喜欢押呢戏辱等无聊游戏。
其他小孩喜欢掩雀捕蝉,戏钱爬树,王充从来不去参与,表现出孤介寡和,端庄严整的气质。
这引起王诵的重视,六岁便教他读书写字,八岁进他上小学。
书馆中学童百余人,都因过失和书法不工遭到先生体罚,唯有王充书法日进,又无过错,未尝受责。
学会写字,王充告别了书馆,开始了儒家经典的专经学习和儒家道德的修练。
《自纪》说:手书既成,辞师,受《论语》、《尚书》,日讽千字。
经明德就,谢师而专门,援笔而众奇。
可见王充接受的正规教育仍然是儒家的伦理,使用的系统教材仍然是儒家的经典《论语》、《尚书》,与常人并无两样。
乡学既成,王充乃负笈千里,游学于京都洛阳。
在洛阳,王充入太学,访名儒,阅百家,观大礼,大开了眼界,大增了学问,初步形成了他博大求实的学术风格。
负笈京师 东汉的京师在洛阳,当时是全国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中心。
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(即光武帝)本是南阳的一位书生,夺得天下后,特别注重文雅,尤向儒术。
史称他“未及下车,先访儒雅”,收集典籍,征招遗隐,“于是四方学士,莫不抱负坟籍,云会京师。
”为了安抚这批饱学通经之士,光武皇帝特起太学,设博士,用他们来教授生徒,造就人才。
太学既是当时全国的最高学府,而且典籍丰富,名流革集,也是全国最权威的学术活动中心。
因此四方郡县都挑选优秀青年进入太学深造,王充亦因成绩优异被保送到太学学习。
王充到太学的时间,大约在建武二十年(公元44年),谢承《后汉书》载:“班固年13,王充见之,抚其背谓班彪曰:‘此儿必记汉事。
’”谢承书已佚,此文见于范晔《后汉书·班因传》李贤注。
班因生于建武八年,比王充小5岁,班固13岁,王充到京师时,已年满18,正当汉光武二十年。
风华正茂,正是学知识,长见识的大好时机。
不过,当时太学受今文经学的影响,盛行章句之学。
传经注重家法师承,先生们将先师的遗教记下,章有章旨,句有句解,称为“章句”。
弟子们反复记诵,味同嚼蜡;恪守师训,不敢越雷池一步。
加之光武皇帝沉迷纬书谶记,事无巨细,皆决于图谶,神学迷信,充斥学坛。
太学教育,不仅方法僵死,而且内容虚诞。
好在这时王充的前辈学者社林、郑众、桓谭、班彪等人都在京师,他们都是古文经学家,博学淹贯,号称大儒。
在数家之中,王充对桓谭和班彪最为推崇,受他们的影响也最深。
在思想方法上,王充又得益于桓谭。
桓谭(公元前23年一公元50年),字君山,沛国相(今安徽濉溪县)人。
“博学多通,遍习五经”,是两汉之际著名学者。
著有《新论》一书。
他治学的特点也是“训诂举大义,不为章句”,与班氏父子学风相同。
在思想方法上,颇具求实精神,喜好古文经学,常与刘歆、扬雄“辨析疑异”,尤其反对当时盛行的谶纬神学,他曾在光武皇帝面前冒着杀头的危险非议谶纬神学,对俗儒的鄙俗见解更是深恶痛绝,常常调笔讥讽,“由是多见排抵”。
桓谭求实的治学精神,王充特别欣赏,他在《论衡》书中多次赞赏说:“(桓谭)又作《新论》,论世间事,辨照然否,虚妄之言,伪饰之辞,莫不证定。
”(《超奇》)“世间为文者众矣,是非不分,然否不定,桓君山论之,可谓得实矣。
论文以察实,则君山汉之贤人也。
”(《定贤》) 王充本来对汉代的董仲舒、司马迁、扬雄等人十分赞赏,但在数家之中,王充对桓谭最为激赏,说“仲舒之文可及,君山之论难追”(《案书》片“彼子长(司马迁)、子云(扬雄)说论之徒,君山为甲。
”(《赵奇》)认为舒仲其文虽奇,犹可学而及之;桓谭出语高峻,非可企及。
甚至与以论说为长的太史公、扬雄相比,桓谭也是首屈一指的。
他说桓谭为汉世学术界值定是非,就像一个公正的执法官一样。
从前汉朝的丞相陈平出佳之前,在阎里“分均若一”,这是能当丞相的象征。
桓谭论议平实如陈平之分物,也是当丞相的料。
可惜他因非毁谶纬,贬死途中。
王充将这位没过过一天丞相瘾的落拓之士称为“素丞相”,以配孔子“素王”;并将桓谭作《新论》与孔子作《春秋》相比美:“孔子不王,素王之业在于《春秋》;然则桓君山不相,素丞相之迹在于《新论》者也。
”(《定贤》)又说“质定世事,论难世疑,桓君山莫上也。
”(《案书》)评定世间的事情,讨论世间疑难,没有一个比得上他。
受桓谭的影响,王充对神学迷信、俗说虚妄也深不以为然,他后来撰著《论衡》一书,其主旨也是“解释世俗之疑,辨照是非之理”(《对作》),与桓谭《新论》的主题如出一辄。
当时在京师的青年学者除班因外,还有贾逵、傅毅、杨终等,俱曾为官兰台,王充也与他们有所往来。
兰台是东汉的皇家图书馆和国家史馆,在那里读书作文,皆由公家供应纸墨,条件优越,待遇优厚,是一个清高又实惠的学术机构,因此时人称进入兰台为登蓬莱,世以为荣。
贾逵,字景伯,扶风平陵人,东汉歹(的古文经学家。
其父贾徽尝从刘歆习《左氏春秋》。
逵少承庭训;通《左传》及五经本文。
《后汉书》本传又说他“自为儿童,常在大学,不通人间事”,是一个兼得家庭教育和太学教育双美的幸运儿。
他博通五经,兼明今古,对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周礼》尤其专门,特别是对《左传》的兴旺发达,功劳甚大。
同时他对于今文家的《大夏侯尚书》、《谷梁传》也十分精通。
他还是汉代第一个遍注群经的大儒,史书说“逵所著经传义诂及论难百余万言,学者宗之,后世称为通儒。
”明帝时,拜为郎官,与班固同在兰台校书。
傅毅,字武仲,扶风茂陵人,少博学,水平中在平陵习章句,深为章句之学的破碎支离所苦恼,因作《迪志诗》,以殷高宗贤相傅说后裔自居,说:“先人有训,我讯我诰。
训我嘉务,诲我博学。
”遂以大义文采为务,斐然成章。
章帝时,授兰台今史,与班贾同业,杨终,字子山,蜀郡成都人。
年13为郡小吏,太守遣至京师习《春秋》。
后随郡上计吏至京师,见三府为《哀牢传》不成,杨终因来自四川,熟悉西南民族情况,作传上之,今天《后汉书·南蛮西南夷列传》中的《哀牢传》就是杨传的改编本。
明帝奇其才,征诣兰台,拜校书郎。
班贾傅杨,俱为同学少年,风华正茂,共在兰台,酬酌诗文,好不风光!
明帝水平十七年,五色雀群集,明帝下诏群儒学士各献《神雀赋》。
百官众僚,纷纷响应,结果只有他们四人和侯讽的赋受明帝欣赏。
王充记其事曰:“永平中,神雀群集,孝明诏上《神雀颂》。
百官颂上,文皆比瓦石,唯班固、贾逵、傅毅、杨终、侯讽五颂金玉,明帝览焉。
”(《侠文》) 王充亲睹其盛,好不羡慕!
一再赞美说:“兰台之史,班固、贾逵、傅毅、杨终,名香文美。
”(《别通》)到了晚年,穷居陋巷,还希望朝廷有朝一日也把他王充征在兰台,“蹈班、贾之迹”,一则以还平生未遂之愿,二则以“论功德之实”(《须颂》),报主隆思。
博览百家 王充在洛阳除了从名师,交胜友外,还广沙博览,穷读群书。
《后汉书》说王充在洛阳,“家贫无书,常游洛阳市肆,阅所卖书,一见辄能诵忆,途通众流百家之言。
”在熟读经史之余,王充还兼及百家,通诸子之学。
浅学俗儒多拘守经本,认为经为圣人所造,是真理所在,皓首穷经;一经之中,又专守一师之说,抱残守缺,排斥异己。
更莫说儒书以外的诸子百家了。
因此他们目光短浅,见解鄙俗。
王充通过对儒书与诸子百家的对比研究,认为诸子与儒经同等重要,有时子书甚至比经书还为可靠。
他说:五经遭秦朝“燔烧禁防,伏生之徒,抱经深藏”,汉兴,“经书缺灭而不明,篇章弃散而不具”、晁错之徒受经于伏生,自后名师儒者,“各以私意,分析文字”,师徒传相授受,形成了所谓的家法和师法。
经书本身的正误已难以辨别,更莫说经师讲解的是是非非了。
相反的是,“秦虽无道,不播诸子”。
由此看来,经书有遗篇,而诸子无缺文。
孰劣孰优就不辩自明了。
王充认为:“诸子尺书,文篇俱在,可观读以正说。
”王充说:圣人作经也有文献依据,“六经之作皆有据”。
由此言之,“书(于史)亦为本,经亦为末。
末失事实,本得道质”。
可见诸子群籍,还是经书赖以造作的依据,哪么正可据之以定正经书。
因此他说:“知屋漏者在字下,知政失者在草野,知经误者在诸子。
”就像立身屋檐底下知道屋漏,身处草莽看得清政治得失一样,读读诸子百家的书,就容易看出经书的错误。
可是章句之儒只知信守师说,鹦鹉学舌地“师师相传”,代代相袭,殊不知“初为章句者,非通览之人也”(《书解》)。
这是就经与子的关系来说的。
从一个希望成为心胸开阔、知识渊博的人来说,博涉经书以外的众流百家更显必要。
他形象地比喻说:“涉浅水者见虾,其颇深者察鱼鳖,其尤深者观蛟龙。
”所涉历的程度和深浅不同,其所见闻和收获自然也不同。
他说做学问也是如此:“入道浅深,其犹此也。
浅者则见传记谐文,深者入圣室观秘书。
故人道弥深,所见弥大。
”他又比喻说:人们游历都想进大都市,就是因为“多奇观也”。
而“百家之言,古今行事,其为奇异,非徒都邑大市也。
”他又说:“大川相间(兼),小川相属(归属),东流归海,故海大也。
”倘若“海不通于百川,安得巨大之名”?
人做学问也是如此,“人含百家之言,犹海怀百川之流也。
”(《别通篇》)其渊博的知识就会自然而然形成。
王充经子并重,博涉众流的特点,正是他成就其博学通才的原因之一。
王充还注意训练自己通博致用和造书属文的能力,他将当时儒学之士分为四等,即:儒生、通儒、文人、鸿儒,他说:“能说一经者为儒生,博览古今者为通人,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,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。
”并且认为:“儒生过俗人,通人胜儒生,文人逾通人,鸿儒超文人。
”(《超奇》)儒生托身儒门,治圣人之经,学圣人之道,远远胜过不学无术的俗人;但儒生仅能死守一经,不知世务,不通古今,“守信师法,虽辞说多,终不为博”(《效力》),故不及博览古今的通人;通人识古通今,诚然可贵,王充曾说过:“知古不知今,谓之陆沉;知今不知古,谓之盲瞽。
”(《谢短》)但是识古通今,只是一种知识的象征,只要“好学勤力,博闻强识”即可做到,能力如何不得而知。
如果“通人览见广博,不能摄以论说,此为匿书主人”,好像那藏书家有书不能观读一样,他认为:“凡贵通者,贵其能用之也”,如果学而不能用,“虽千篇以上,是鹦鹉能言之类也。
” 文人能草章属文,正是“博通能用”的人,故贵于通人。
但是,文人仅能作单篇文章,不能“连结篇章”,写成专书,所以不及能写长文大著,自成一家之言的鸿儒。
他认为鸿儒最为珍贵,如果说文人是知识分子中的超人奇士的话,那么鸿儒就是“超而又超”,“奇而又奇”的特级人物,若与儒生相比,就好像装饰华美的车子与破车,锦绣与旧袍子相比一样;如果与俗人相比,更是犹如泰山的山顶与山脚,长狄的颈项与脚掌一样,具有天壤之别!
他们是人中超奇,“世之金玉”。
(《超奇》)汉代的谷永、唐林,能上书言奏,依经论事,属于“文人”;而董仲舒、司马迁、扬雄、刘向、刘歆、桓谭等人能鸿篇大论,著书立说,则是“鸿儒”。
王充把他们与圣人同科,视为稀世之珍:“近世刘子政父子、杨子云、桓君山,其犹文武周公并出一时……譬珠玉不可多得,以其珍也。
”(《超奇》)王充对鸿儒如此看重,自然他的努力方向也就是成为一名为世所贵的鸿儒了。
他师事班彪,不守章句,博览百家……都是通往鸿儒之路的有效措施。
王充在京师游学历时多久,史无明文,袁山松《后汉书》说王充赶上了汉明帝临辟雍的盛典:充幼聪朗。
诣太学,观天子临辟雍,作《大儒论》。
袁山松书已佚,这条材料见于李贤《后汉书注》。
注文作《六儒论》,根据王充推崇鸿儒的思想,“六儒”当为大儒之误。
辟雍,周代为太学之一,汉代则作为尊儒学、行典礼的场所。
据《后汉书·儒林列传》,东汉辟雍始建于光武皇帝中元元年(56年),尚未来得及亲临其境,光武帝便驾崩了。
到了“明帝即位,才亲行其礼。
”《明帝纪》说,水平元年(58年)十月“幸辟雍”,那么,至少在永平元年,王充尚在京师,其时他已32岁,在洛阳访学已经14岁。
明帝在即位之年,恢复了许多久废的儒礼,以表示对礼治的提倡。
这年正月,皇帝戴上九寸高的通天冠,穿上绣着日月星辰的礼服,先祭光武皇帝于明堂,既而登灵台,望云物,吹奏迎春的乐曲,观察物候的变化,制定《时令》书,颁给列侯、诸王,重演了一番早为孔子所叹惜的授时“告朔之礼”。
这年冬天,明帝又亲临辟雍,举行尊老养贤之礼。
事先推定年老博学的李躬为“三老”,曾授明帝《尚书》的桓荣为“五更”,这天,天子先行到达辟雍,举行典礼,然后派人用安车蒲轮(用蒲草裹轮以免巅簸)将三老五更接来,皇帝亲自到门屏之间迎接。
以宾主(而非君臣)之礼迎上柞阶。
皇帝下诏“尊事三老,兄事五更”,三公九卿,各就各位。
皇帝挽起龙袍,操刀亲割,将肉献(不是赐)给三老,还亲自给他酌酒;五更,则由三公如此这般地侍候。
接着举行射礼,射礼完毕,明帝归坐于讲堂之上,正襟危坐,执经自讲,诸儒执经问难于前。
不够级别的“冠带缙绅”,只有环绕着辟雍璧水,隔岸观望了。
这天,平时被人骂为穷酸腐儒的儒生算是扬眉吐气了一回。
王充看到了这出从前只在礼书上记载着、在儒生们口头传诵着的敬老尊儒大典,无疑是十分兴奋的,于是欣然作《大儒论》以颂其事。
就是事隔数百年后,范晔作《后汉书》,在写到这一盛况时,也不无激动地说:“(明帝)坐明堂以朝群后,登灵台以望云物,袒割辟雍之上,尊事三老五更……济济乎!
洋洋乎!
盛于永平矣。
”仕途落拓 和所有的读书人一样,王充学成之后,也曾抱着致君尧舜的梦想,走“学而优则仕”的路子。
可是王充在官场的境遇并不比他的老师们好多少,《自纪篇》自叙其为官履历曰:在县,位至掾功曹;在都尉府,位亦椽功曹;在太守,为列掾五官功曹行事;入州为从事。
王充一身只当过地方官,东汉地方机构,实行州、郡、县三级制,王充历仕三级,但都位不离“掾”。
掾,是汉代各极机构中的属官。
在县里,他作官至掾功曹,主管一县人事和考功。
在郡里,他曾先后在军事长官都尉府作过掾功曹,在行政长官太守府代理五官曹和功曹。
在州里,他亦被州刺史征辟为从事属官。
生平就没逃脱过为人下僚的命运。
王充为官的地方,可考知者有扬州、丹阳、九江、庐江等地,《自纪篇》曰:“充以元和三年(86年)徙家辟诣扬州部丹阳、九江、庐江,后入为治中。
材小任大,’职在刺割。
章和二年(88年),罢州家居。
”这条自纪《北堂书钞》卷73和《太平御览》卷602引作“章和二年,徙家避难扬州丹阳。
”有误,“章和二年”应作元和二年,章和二年是充自免家居年,非始往之年。
辟,指征辟,被征去作官,不是避难。
《后汉书》亦载:“刺史董勤辟为从事,转治中,自免还家。
”辟字正作征辟讲。
扬州是汉武帝所置十三部(州)之一,东汉为郡上一级行政机构。
丹阳、九江、庐江皆郡名,当时属扬州部所辖。
在元和三年值钱前,王充为任何所尚不清楚。
刘汝霖《汉晋学术编年》建初元年条,根据王充《对作篇》“建初孟年,中州颇歉,颍川汝南,流民四散,圣主忧怀,诏书数至,《论衡》之人,奏记郡守,宜禁奢侈,以备困乏。
言不纳用,退题记草,名曰《备乏》”的自述,遂怀疑“充所仕者非在会稽而在中州之郡邪?
”但别无旁证,难成定论。
造成王充这种徘徊州县,淹滞不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,后来王充结合自己的切身体会,曾对仕路穷通作过全面的分析和论述。
《逢遇篇》将入仕宦的达与不达归结为遇与不遇:操行有常贤,仕宦无常遇。
贤不贤,才也;遇不遇,时也。
才高行洁,不可保以必尊贵;能薄操浊,不可保以必卑贱。
或才高行洁,不遇,退在下流;薄能浊操,遇,进在众上。
世各自有以取士,士亦各自得以进。
进在遇,退在不遇。
处尊居显,未必贤,遇也;位卑在下,未必愚,不遇也。
古人常说“千里马常有,伯乐不常有”,贤才常有,但仕宦的机会不常有。
生逢其时,仕遇其主,虽才浅德薄也因缘得进;反之,如果生不逢时,所遇非人,即使才高八斗,德比夷齐,也会落拓在野,沉沦下僚。
这在缺乏健全的竞争机制时更是如此。
不过王充生当光武、明帝、章帝、和帝之世,正是东汉王朝的上升时期,征辟举拔之制,还是比较正常的,似乎谈不上生不逢时的问题,但并不排除其所遇非人的可能。
《后汉书》说他“仕郡为功曹,以数谏争不合去”。
王充也曾自纪建初初年,中州欠收,充曾上书郡守,主张厉行节俭,以备困乏,但“言不纳用”;时俗嗜酒,充以为酒耗五谷,又有醺酒滋事之忧,奏记郡守:主张“禁酒”,亦不被重视。
读书人的看家本领就是建言献策,既然言不纳用,可见他遇到的确实并非知己。
王充在《累害篇》中又提出“累害”说:凡入仕宦有稽留不进,行节有毁伤不全,罪过有累积不除,声名有暗昧不明,才非下,行非悖,又知(智)非昏,策非味也,连遭外祸,累害之也。
仕宦留滞,行迹诬伤,有罪不除,声名狼狈……这一切并不一定是他本人的过错,很可能是外物的连累和陷害。
王充将这些来自外物的毁伤归纳为“三累三害”。
何谓三累三害?
充说:乡里有三累,朝廷有三害。
乡之三累指仕宦之前遇到的麻烦:朋友反目,相为毁伤,一累也;庸才忌妒,毁伤高才,二票也;交游失和,转相攻击,三累也。
朝之三害指出佳之后遭受的陷害:竟进者为了有限的职位互相诋毁,在长官面前捏造夸大事实,长官又不明察,信纳其言,一害也;同僚爱好不同,清浊异操,“清吏增郁郁之白,举涓涓之言”,名声越来越洁白,见解越来越高明,浊吏自惭形秽,怀恨在心,暗中收集清吏的过失,陷害重罚,二害也;长官亲幸佐吏,佐吏人品不高,提拔邪回之人,对不肯附从的“清正之士”必然心怀不满,在长官面前诋毁他,三害也。
王充所举的三累三害,生动而具体,恰如自己的切身遭遇。
王充是东汉时期杰出的思想家,唯物主义哲学家。
整个东汉二百年间,称得上思想家的,仅有三位:王充、王符、仲长统。
王符(公元85—162年),字节信,著有《潜夫论》,对东汉前期各种社会病端进了抨击,其议论恺切明理,温柔敦厚;仲长统(公元180年—220年),字公理,著有《昌言》,对东汉后期的社会百病进行了剖析,其见解危言峻发,振聋发聩。
王充则著《论衡》一书,对当时社会的许多学术问题,特别是社会的颓风陋俗进行了针砭,许多观点鞭辟入里,石破天惊。
《论衡》也可以说是我国古代的一部“百科全书”。
就物理学来说,王充对运动、力、热、静电、磁、雷电、声等现象都有观察,书中记载了他的观点。
他还解释了人与自然的关系。
王充把人的发声,比喻为鱼引起水的波动;把声的传播,比喻为水波的传播。
他的看法与我们今天声学的结论是一致的:声是物体振动产生的,声要靠一定的物质来传播。
欧洲人波义耳认识到空气是传播声音的媒介,是17世纪的事,比王充晚1600年。
范晔《后汉书》将三人立为合传,后世学者更誉之为汉世三杰。
三家中,王充的年辈最长,著作最早,在许多观点上,王充对后二家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,王充是三家中最杰出,也最有影响的思想家。
但是由于王充在书中对传统的儒学,特别是汉代经学,进行了论难,有时甚至怀疑古经,上问孔孟,著有《儒增》《书虚》《问孔》《刺孟》等专篇,公然向神圣的经典挑战,向孔孟圣贤发难,这就有犯天下之大不韪,因而被视为名教之罪人。
清乾隆皇帝御批:王充“刺孟而问孔”,“已有非圣无法之诛!
”其他学人虽然不能治其“非圣无法”之罪,但也多挥毫濡翰,口诛笔伐。
素以危言危行著称的大史学家刘知几,因《论衡》书中记载了王充父祖横行乡里的不光彩行径,不合乎子为父隐的纲常名教,说王充“实三千之罪人”!
章学诚亦对王充非难儒学的作法,对他的儒家身份提出了质疑。
自《隋书·经籍志》以下,历代目录书都将王充《论衡》列入无所宗师的“杂家”类。
近代经学大师刘师培又说王充是“南方墨者之支派”。
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,在中国学坛上又曾有人说王充是儒家的反对派,是反孔的急先锋……凡此等等,不一而足。
自然我们今天不必为这些带有浓厚政治偏见的褒贬,去为古人的恩恩怨怨纠缠不休,但是,从学术的角度看,我们认为不能仅凭“问孔、刺孟、非儒”这些表面现象就断定他的学术派别,而应视其所问、所刺、所非的具体内容。
根据王充的整体思想来分析定性,笔者认为:综观王充的一生言行,他不仅是一位儒者,而且是一位博学的奇儒。
梁启超在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中称:“王充《论衡》实汉代批评哲学第一奇书。
”黄侃在《汉唐玄学论》一文中说:“东汉作者,断推王充。
《论衡》之作,取鬼神、阴阳及凡虚言、谰语,摧毁无余。
自西京而降,至此时而有此作,正如久行荆棘,忽得康衢,欢忭宁有量耶”(《黄侃论学杂著》)?
由此可见王充与《论衡》在近现代学者心目中的地位。
近年笔者有《论衡词典》编撰之役,在选择底本、搜集资料中发现:第一,近现代学者眼中如此重要之书,在整个有清一代,竟无像样的版本。
第二,校注成果寥寥,竟无有一部完整的校注本。
中国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经、史、子、集有代表性的重要著作,大都经过了清代学者的校注整理,不少重要典籍甚至有多个校注本问世,《论衡》一书却几乎无人问津,没有一部新的校注本出现。
笔者心中遂生一疑团:清代学者心目中的王充与《论衡》和今人一样吗?
如果一样,那么他们为何对《论衡》如此冷漠,既不刊刻又不整理?
是偶尔疏忽还是另有原因?
原来,清代学者心目中的王充与《论衡》,和现代学者大不相同。
在清代学者眼里,王充实在是一个不孝之人。
王充的不孝,首先表现在自述父祖的劣迹。
王充介绍自己的家世时说:“世祖勇任气,卒咸不揆于人。
岁凶,横道伤杀,怨仇众多。
会世扰乱,恐为怨仇所擒,祖父泛举家担载,就安会稽,留钱唐县,以贾贩为事。
生子二人,长曰蒙,少曰诵。
诵即充父。
祖世任气,至蒙、诵滋甚,故蒙、诵在钱唐,勇势凌人。
末复与豪家丁伯等结怨,故举家徙处上虞。
”通过王充的记述,我们可以看出,王充的祖上,连续数辈,横行乡里,仗势欺人,时常犯有命案,结怨甚多,因担心仇家报复,不得不数度迁徙,可谓是违法乱纪的恶霸。
以我们今人的眼光看来,王充的作法可以说是不避家丑、实事求是。
但在“臣为君讳、子为父讳”的封建社会里,被视为是一种不孝之举,便不足为奇了。
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在《潜研堂文集·跋〈论衡〉》中批评王充的罪过之一,便是“《自纪》之作,訾毁先人。
”其实早在唐代,史学家刘知己在《史通·序传》中就已指出:“王充《论衡》之《自纪》也,述其父祖不肖,为州闾所鄙……夫自叙而言家世,固当以扬名显亲为主,苟无其人,阙之可也。
”王充之所以毫不忌讳地言其父祖的劣迹并不奇怪,因为从王充的思想深处来看,孝的意识十分淡薄。
人们之所以会形成孝的观念,主要是出于对父母生育之恩的感激。
在王充看来,父母生儿育女,完全是性欲冲动的结果。
他在《论衡·物势篇》中说:“夫天地合气,人偶自生也,犹夫妇合气,子则自生也。
夫妇合气,非当时欲得子,情欲动而合,合而生子矣。
”王充所言虽然有一定道理,但把父母生子完全看作是为了满足性欲的要求而非有意识的行为,便很难产生出孝的观念,因而其有诋毁父祖的言论,也就不难理解了。
王充的不孝,最被人所诟病者在于扬己抑祖。
他在《自纪篇》中一方面贬毁祖辈,另一方面极力标榜自己,说自己自小便与众不同,仁义听话,恭敬有礼,“父未尝笞,母未尝非,闾里未尝让,”喜欢学习,成绩突出。
成年之后,更是品德高尚,淡薄名利,“常言人长,希言人短”,“得官不欣,失位不恨。
处逸乐而欲不放,居贫苦而志不倦。
”“为人清重,”“性恬澹,不贪富贵”,简直完美无瑕,无可挑剔,与其劣迹斑斑的祖上,形成了鲜明对比。
尽管如此,王充卑微的出身,祖上不光彩的形象,始终是他一块难以消除的心病。
于是他便从历史上寻找证据,来说明父祖不好,并不影响后人成才,以此洗刷自己。
他《自纪篇》中说:“母骊犊騂,无害牺牲;祖浊裔清,不%奇人。
鲧恶禹圣,叟顽舜神;颜路庸固,回杰超伦;孔、墨祖愚,丘、翟圣贤。
”清代著名学者惠栋,在“母骊犊騂,无害牺牲;祖浊裔清,不%奇人”之后加批语云:“自誉而毁其先,非人也”(王欣夫《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》)。
钱大昕《十驾斋养新录》卷六“王充”条针对这段文字说:“盖自居于圣贤而訾毁其亲,可谓有文无行,名教之罪人也。
”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亦云:“至于述其祖父顽很,以自表所长,傎亦甚焉。
”可见,无论是官方,还是清代学者个人,都认为王充是一个毁祖誉己的小人和破坏名教的千古罪人。
在“天下之事孝为上”、孝“为万事之纲纪”的观念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里,谁愿意整理、刻印一个不孝之子的著作呢?
知道了这一点,清代学者不刊刻、不校注《论衡》,便很容易理解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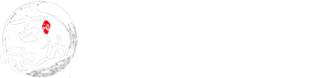
 用户中心
用户中心


